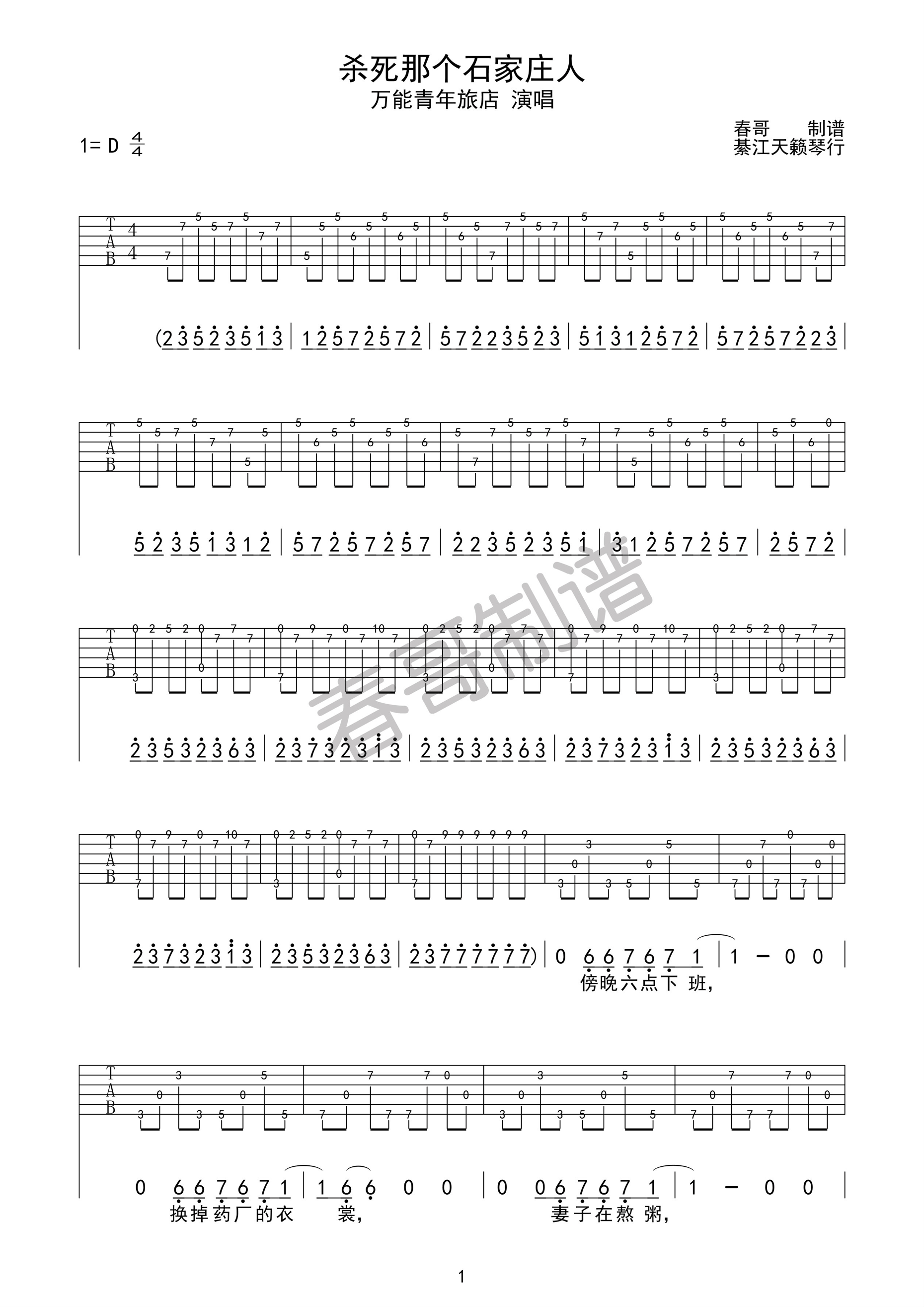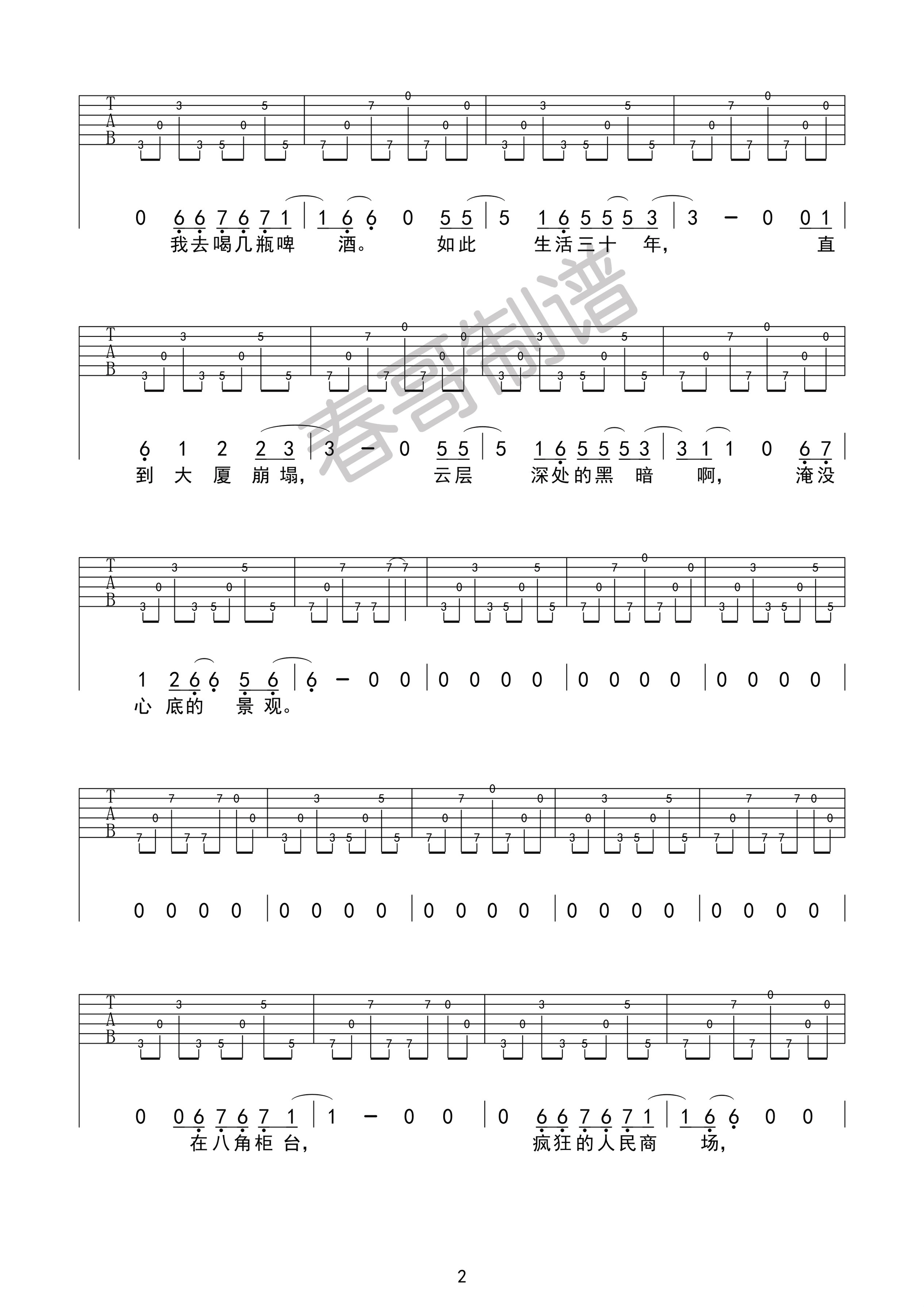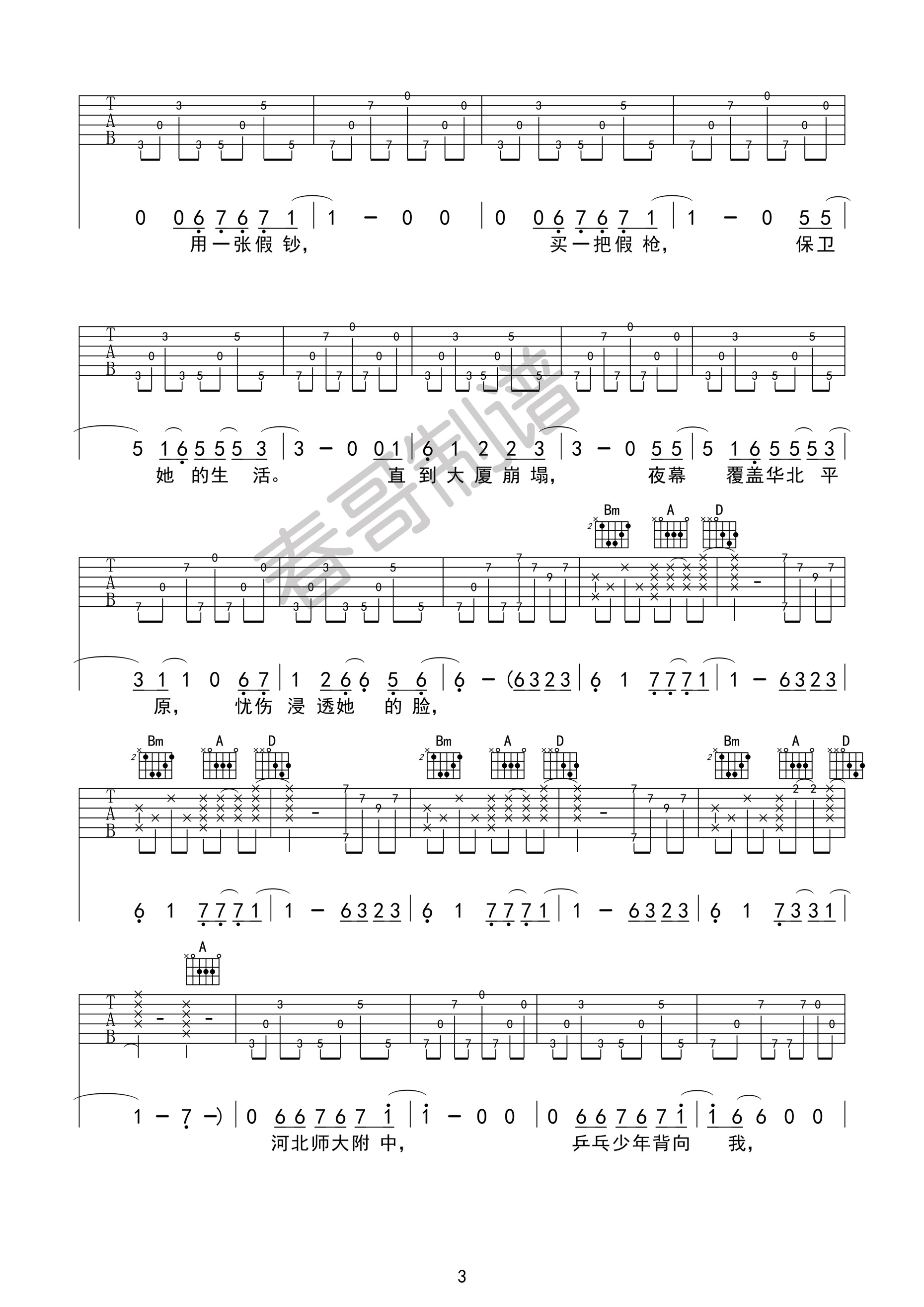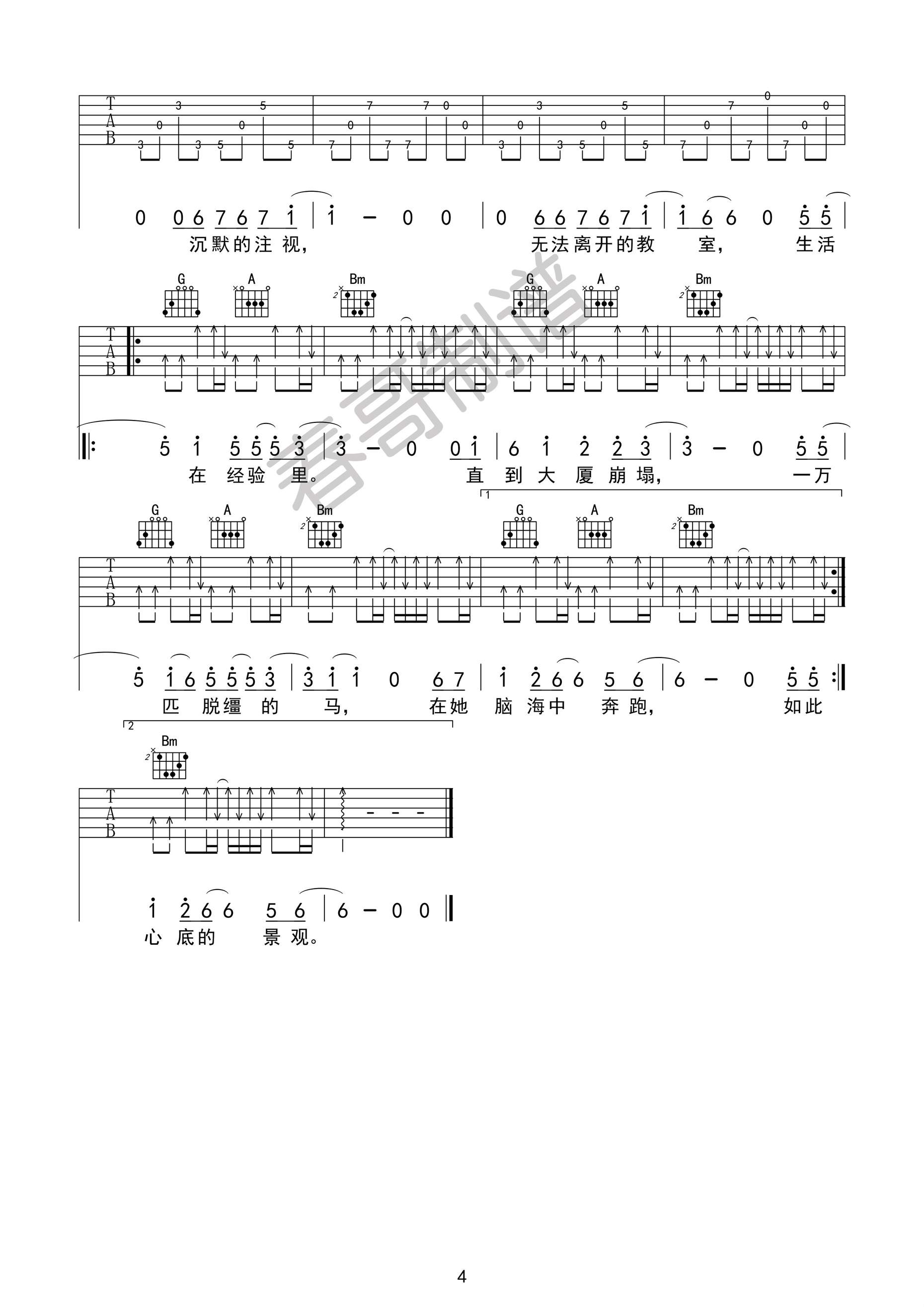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以冷峻的笔触勾勒出工业化浪潮下个体的生存困境,歌词中反复出现的药厂、家庭、电视机等意象构成一幅世纪末的北方工业城市浮世绘。破碎的婚姻关系与僵化的工作日常形成双重枷锁,用“如此生活三十年”的循环句式直指时间流逝中的精神钝化。夜幕降临后的假钞交易与暴力冲动,实则是被体制规训后扭曲的情感宣泄,歌名中的“杀死”并非物理层面的谋杀,而是对麻木灵魂的象征性处决。乒乓少年与大厦崩塌的意象并置,既暗喻理想主义的脆弱性,又揭示经济转型期集体信仰的溃散。歌词将私人记忆与时代阵痛焊接,电视机里播放的乌云典当行既是个体记忆的存储装置,也是整个时代价值混乱的隐喻。那些反复擦拭的步枪最终指向自我,在工人新村褪色的墙皮后,埋葬着无数未被言说的愤怒与失落。整首作品如同用手术刀解剖的标本,在家庭解构、国企改制、信仰真空的截面里,暴露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,普通人承受的隐秘精神创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