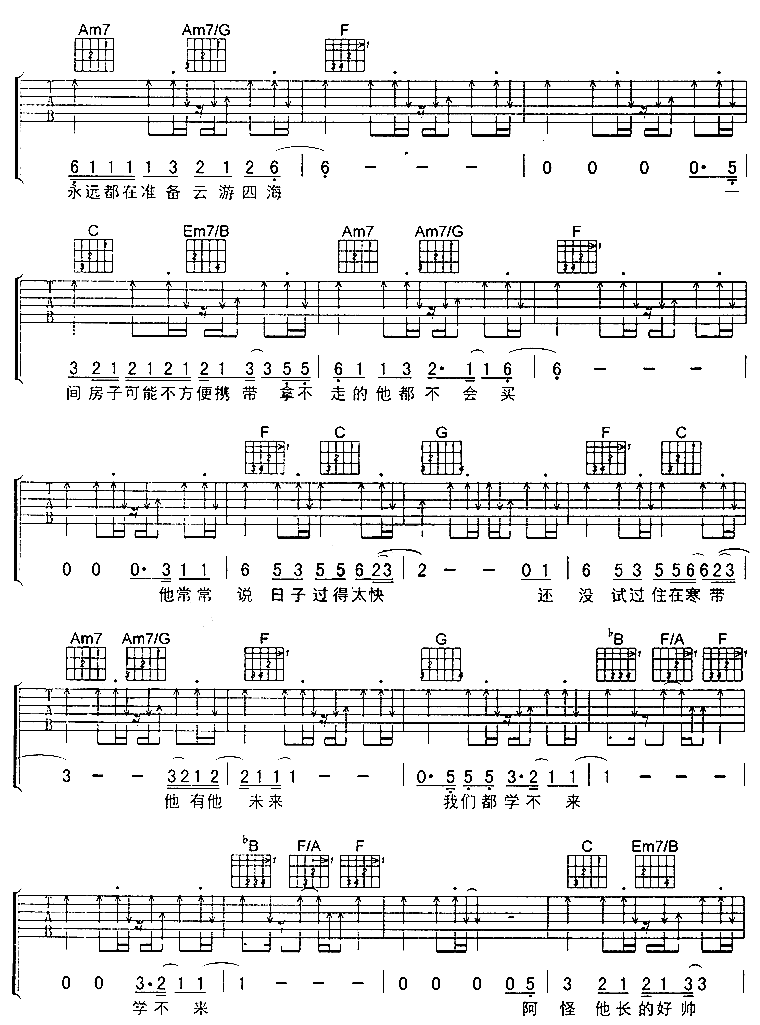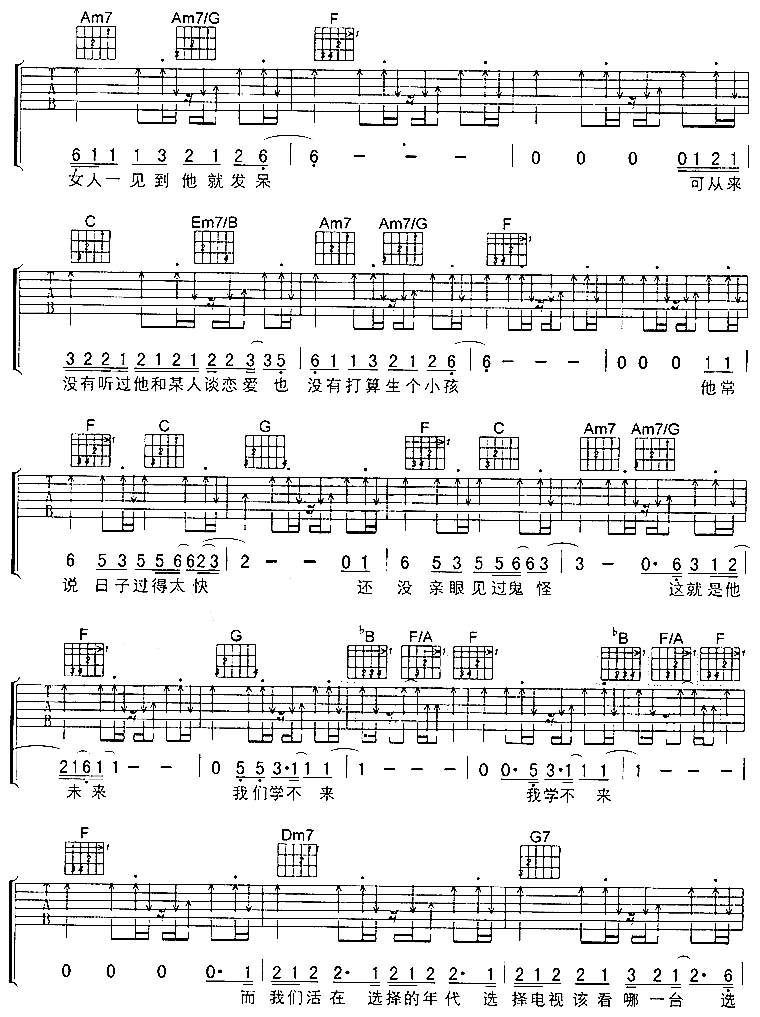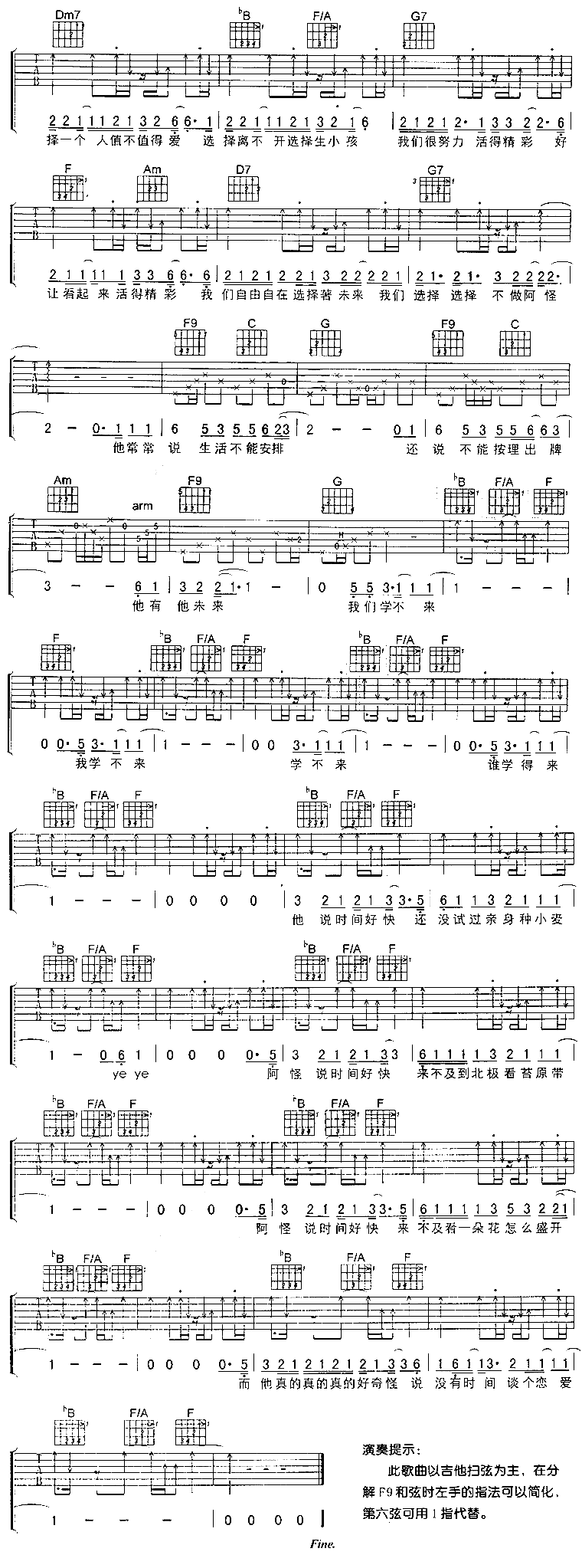《阿怪》以荒诞戏谑的笔触勾勒出一个游离于社会规则之外的边缘人形象,通过黑色幽默的叙事展现现代文明中的异化现象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阿怪"既是具体人物又是象征符号,其非常规的行为模式——用咖啡浇花、拿熨斗烤面包、穿着西装遛狗——构成对标准化生活的温柔反叛。这些看似滑稽的生活细节实则是存在主义的隐喻,揭示个体在高度程序化社会中遭遇的精神困境。歌词刻意模糊正常与异常的界限,当叙述者反问"到底谁是阿怪"时,实质质疑的是主流价值体系的评判标准。电子表与机械表的意象对立暗示科技时代人与传统的割裂,而"把路灯当月亮"的错觉则呈现出现代都市人的精神恍惚状态。作品通过阿怪这个"城市漫游者"的形象,探讨了在高度同质化的都市空间里保持个性自由的代价,那些被定义为怪诞的行为背后,可能隐藏着未被理解的孤独与拒绝妥协的坚持。结尾处阿怪的消失留下开放式思考:当异类选择隐没于人海,究竟是社会的包容还是个体生命力的消解?歌词以诙谐的寓言方式完成了对现代性困境的严肃叩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