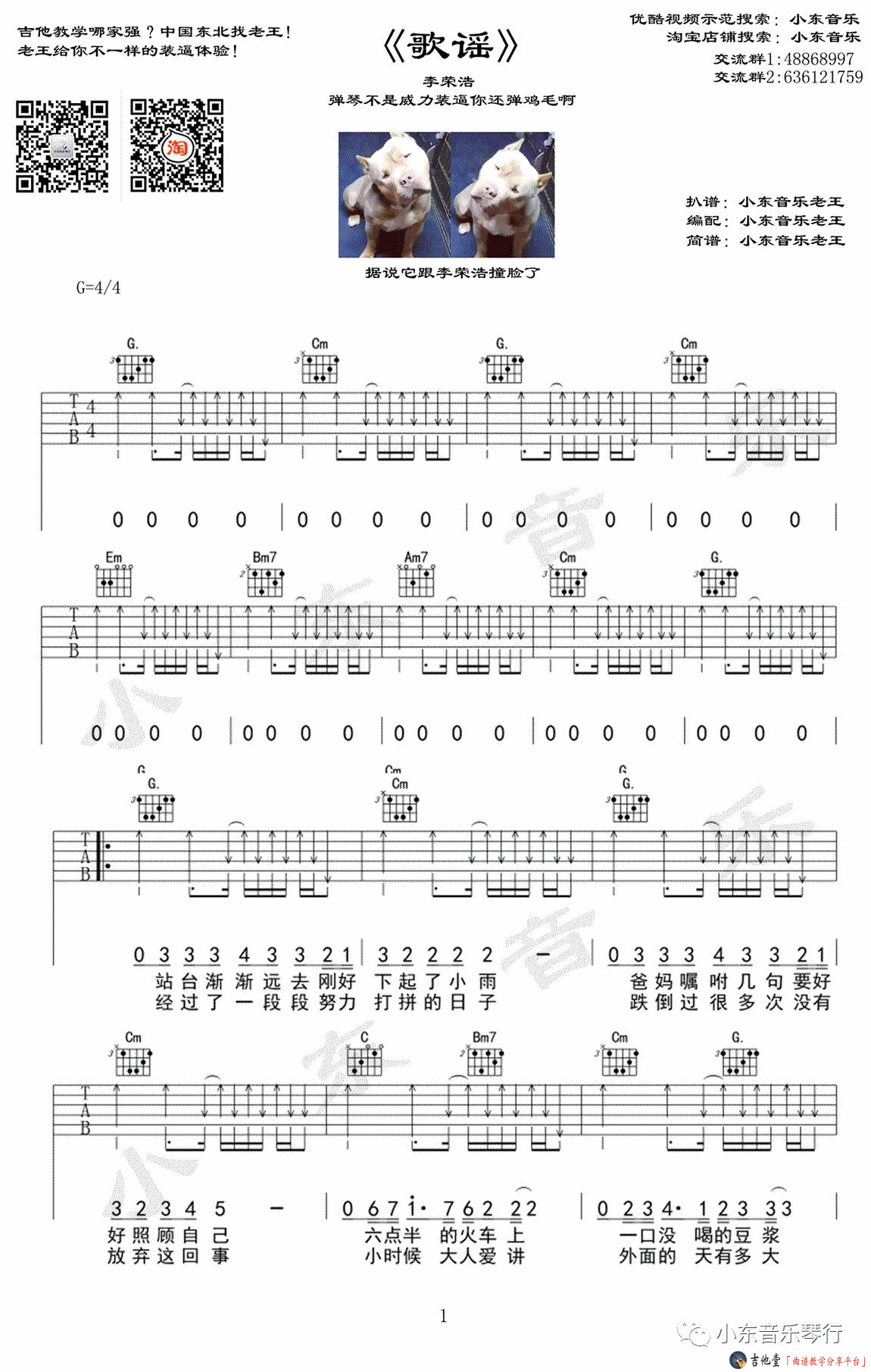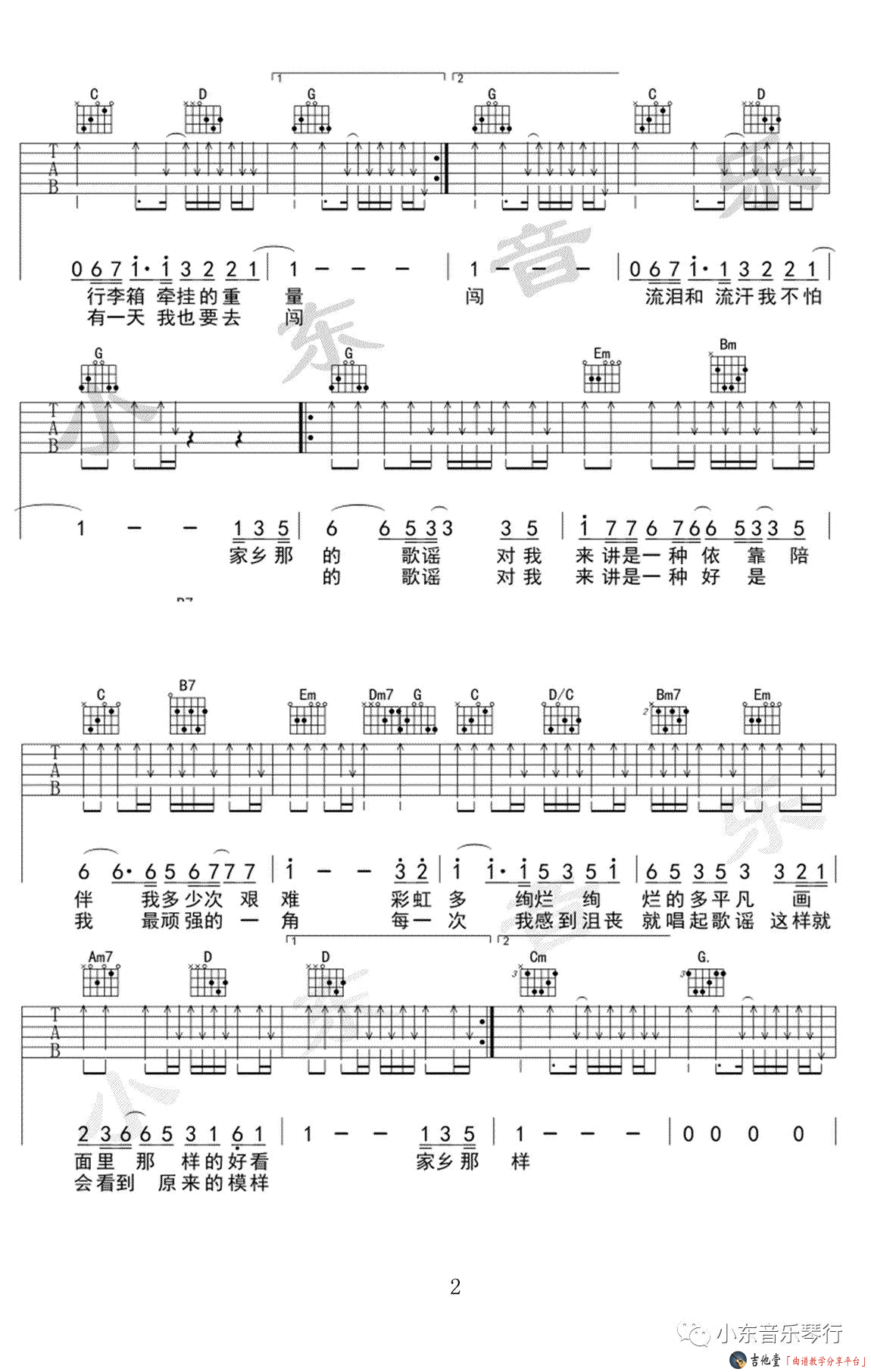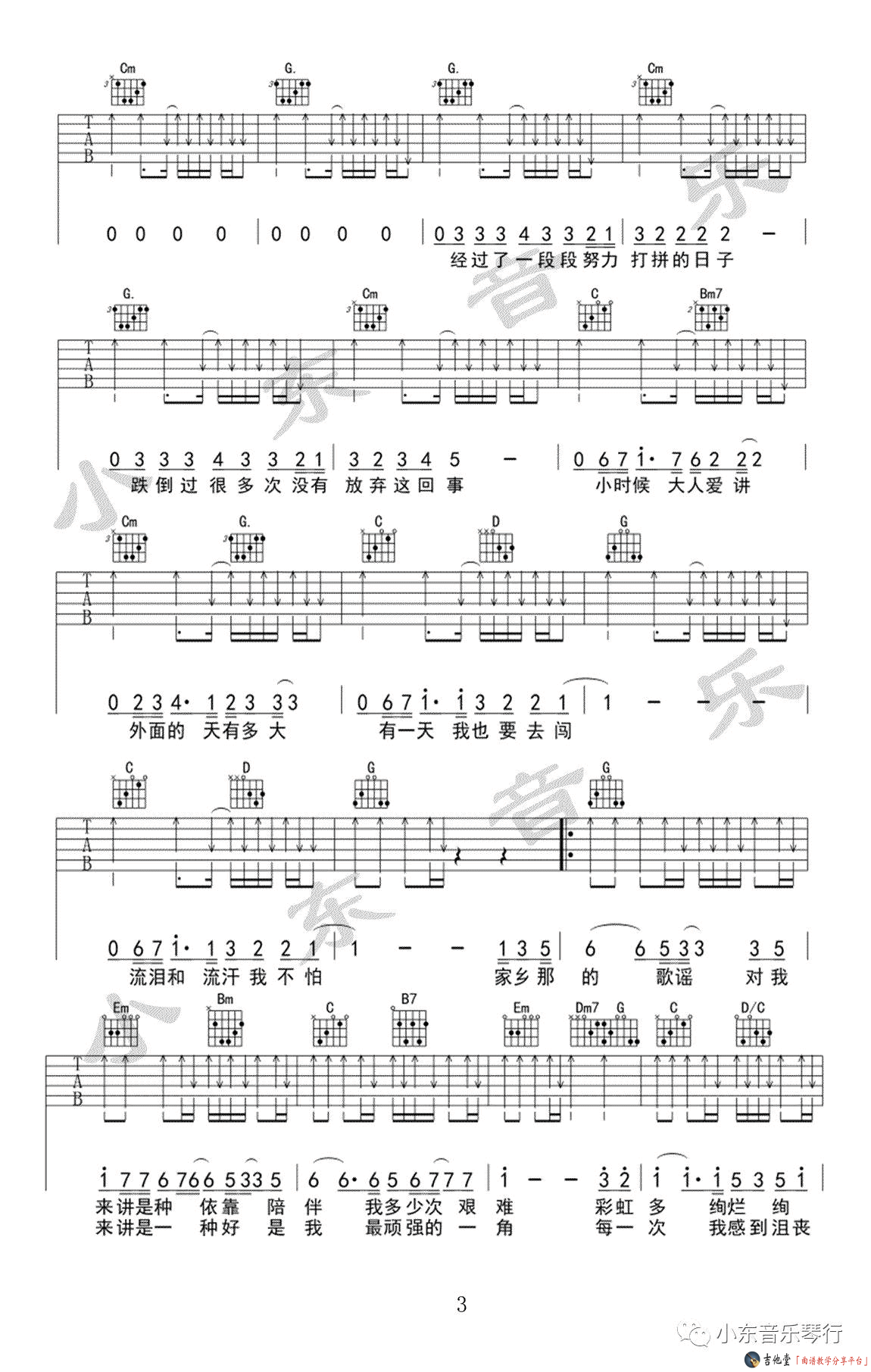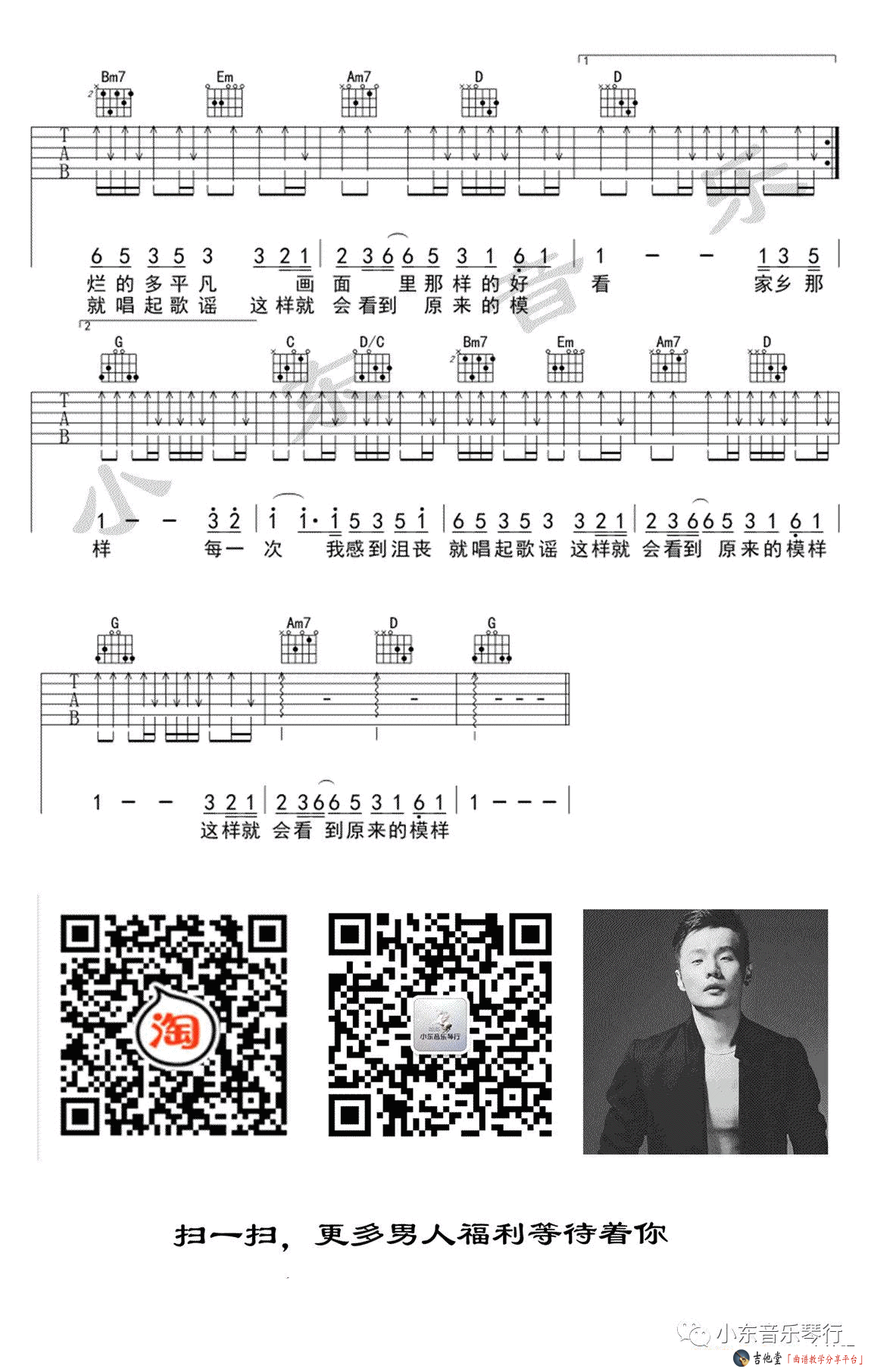《歌谣》以质朴的语言勾勒出岁月流转中永恒的情感纽带,通过意象的层叠展现生命与记忆的交织。屋檐雨滴、炊烟、蒲扇等日常物象被赋予诗性光芒,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容器,在重复的"轻轻唱"中构建起代际传承的韵律。歌词中自然时序与人生节律形成隐秘共振,三月的风与十月的霜既是环境变迁的见证,也是生命不同阶段的隐喻。歌谣本体被塑造成超越时空的存在,既是具体的民间艺术形式,又是抽象的情感载体,在口耳相传中完成对抗遗忘的仪式。青石巷与红砖墙的意象并置暗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,而始终如一的吟唱声则成为文化基因的显性表达。结尾处"故事在泛黄/歌谣在发烫"的悖论修辞,揭示出记忆载体与情感温度的反向生长关系——物质性终将褪色,精神共鸣却因不断传唱而持续升温。整首作品通过歌谣这个文化符号,完成对民间生命力与永恒乡愁的双重书写,在回环往复的韵律中抵达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结构。